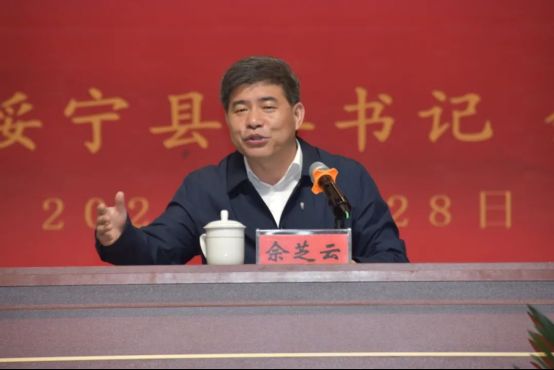绥宁作家(三) 来源:绥宁一中校园网 作者:夏宏俊 更新时间:2012-4-12 阅读:37040次 |
||
蜜蜂飞来飞去(小说) 陶永灿 (一) 翎子起床的时候,妈妈还没有醒。昨晚,妈妈又咳嗽了,一夜没有睡好。 翎子轻轻拉开门,端起木盆朝河边走去。自从妈妈病了以后,翎子每天早晨都要去河边洗衣,挑水,放鸭子……翎子的家是典型的湘西吊脚楼,像一个土蜂窝粘在半山腰上,去河边要下一个长长的坡,一级一级的石板小路扭过来扭过去,蛇一样抵达河边。 对面的山峦还藏在晨曦中,小鸟还在吱吱地说着梦话。河沟里浮着一层烟一样的雾,什么都还看得不太清楚,只听到河水哗哗啦啦的,在唱一支永远也唱不完的歌。翎子的心情很好,她清清瑶家姑娘特有的嗓子,轻轻唱道: 瑶家姑娘把花爱,我把花名报上来。 正月兰花满山坡,二月李花朵朵白。 三月桃花红似火,四月杜鹃花正开。 …… 唱着唱着,歌声戛然而止。 翎子十分惊异地望着河边。绿色荡漾的河滩上,忽然有了一座房子! 翎子每天都要去河边,但都没有看见房子,怎么一夜之间就长出房子了呢?传说这条河里住着一个善变的妖怪,她能把芭蕉叶变成老婆婆头上的丝帕,能把牛屎变成脸上的黑痣。那座突然出现的房子,是不是河妖变出来的呢? 翎子把木盆咚地放在石级上,转身匆匆跑回屋里。 “妈妈,妈妈,你快去河边看看吧!”翎子把妈妈摇醒。 妈妈无力地起身下床,揉着胸口问:“河边怎么了?” 翎子也不解释,扶着妈妈就走。下到半坡上,母女俩停住了。她们定定地望着河滩,河滩上真的有座工棚样的小房子,旁边还有好多木箱,围成了一个圈。 “养蜂的。”妈妈的声音有些飘。 “养蜂的?”翎子感到又新奇,又吃惊。 “对,他们是养蜂人。”妈妈吃力地说,“小房子是他们住的地方,那些木箱子,是蜂箱。” (二) 河边来了养蜂人!这对翎子来说,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。 翎子的家在一个山湾里,方圆几里没有人烟,平常很少有人到这里来,现在,居然来了养蜂的人。翎子还从没见过养蜂哩,他们是怎么养蜂的呢?蜜蜂又是怎样酿蜜的呢?从此,翎子每次去河边,都忍不住要望望那座小房子,望望那些围成一个圈的蜂箱。 一天,翎子出神地望着小房子时,一双眼睛也在望着她。 那是一个男孩。 男孩戴一顶草帽,帽檐上吊着一层纱巾,好像他很害羞,不想让别人看见他的脸。 “过来玩玩吧。”是男孩发出的邀请。 翎子不怎么想,就过去了。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香香甜甜的味道,好闻极了。无数的蜜蜂嘤嘤嗡嗡的,在空中往来穿梭,飞来飞去。每当蜜蜂飞来,翎子就不停地躲闪。男孩撩起面前的纱巾说:“不用怕,你不伤害它,它不会蜇你的。”男孩撩起纱巾,翎子看清他是一个既英俊又和善的男孩。可翎子还是有些害怕,她跟在男孩身后,男孩到哪,她也到哪。 男孩把蜂箱盖揭开,里面是一层一层的隔板,隔板上爬满了忙忙碌碌的蜜蜂。翎子问男孩说:“它们是怎么酿蜜的呢?” 男孩笑了笑,说:“蜜蜂酿蜜的工作是由工蜂完成的。工蜂飞到蜜源植物上,把花的甜汁儿吸进自己的嗉囊,嗉囊装满后再飞回巢里,把甜汁儿吐出来,然后又出去采集。晚上也不休息,它们把白天采的花蜜吸进自己的蜜胃里,慢慢调制,然后吐出来,又吸进去调制,又吐出来……这样反反复复几百次,才能酿成蜜呢。” 男孩说的时候,翎子“哦哦”地应着,仿佛她听懂了,又好像没有懂。 “什么是蜜源植物?”对翎子来说,这都是一些新鲜名词。 男孩说:“就是有甜汁的花儿。” “那蜜蜂现在采的是什么花呢?” 男孩指指山坡上一片白花说:“刺桐木花。” 这里有一种树叫刺桐木,春天开花的时候,满山遍野白白的,雪天一般,只是刺桐木的花期短,二十来天就谢了。如果采完了刺桐木花,怎么办? “搬家呀。”男孩说。 男孩告诉翎子,他们是从广西来的,他们一年四季在追着花儿跑,春天从海南岛开始,那里有荔枝花,有椰子花,然后到湖南、湖北……一直到内蒙古大草原,草原上的荞麦花可多哩。“哪里有花,哪里就是我们的家。”男孩自豪地说。 那不跟草原上的牧民一样么?牧民们逐草而居,他们是逐花而居。 翎子随男孩来到小房子。小房子很简陋,几根木棍搭成一个骨架,上面蒙着一层油毛毡,里面只有几个木箱和桶子,搁着的几块木板上,胡乱地铺了一层稻草,那是他们的床。 翎子看见床上有一本初中二年级的语文书,顿时眼睛一亮:“你也上初二?” 男孩惊喜地问:“你上初二?” “对!我们是同一个年级。”翎子随手拿起课本,见上面写着“杨力”,就问:“你叫杨力?哦,我叫翎子。” 翎子翻着课本,见字里行间做满了各种标记,就问他们学到哪一课了。杨力支支唔唔的正要回答,门口忽然闪进一个身影。 杨力说:“我爸来了。” 翎子赶紧叫了一声“叔叔”。杨力爸只“唔”了一声,就忙事去了,看都没看翎子一眼。 翎子觉得好没趣,背起猪草篓就走了。 杨力在后面追:“翎子……翎子……” 他爸爸冲出屋子,凶巴巴地喊道:“杨力,你给我回来!” (三) 翎子静静地坐在河边,默默望着河水出神。这条清澈的小河从高高的雪峰山流来,日夜不停地翻着浪花,唱着歌儿,款款地注入沅江,流进洞庭湖……它那欢快的样子,一点也不懂得翎子的愁苦。 这几天,妈妈的病又加重了,总是整夜整夜地咳。差不多半年来,妈妈都是这样,几天不吃药,就无休止地咳。翎子好心疼,可是她有什么办法呢,爸爸好久不寄钱回来了。 过完了年,爸爸就去广东打工了。本来翎子不想要爸爸去打工的,现在国家减免了学费,上学不需要什么钱了,但是去年冬天,妈妈病了。医生说妈妈得的是慢性病,得治疗很长时间,得天天吃药。上次爸爸寄来的钱早花光了,前几天翎子给爸爸打电话,爸爸在电话里说,他刚换了一个新厂,新厂还没有发工资。没发工资哪有钱寄回来呢?没有钱,又拿什么去给妈妈买药呢? 如果河妖能变出药来,那该多好啊!翎子把一颗石子投进河里,溅起一片耀眼的水花。 “翎子。” 这时忽然有人叫她。她回过头来,原来是杨力。 “翎子,那天真对不起!请你不要见怪,我爸他……” 翎子说:“不,杨力,我没有怪你爸。” 杨力说:“那你这几天干嘛不来玩呢?干嘛一个人到河边来发呆呢?” 翎子幽幽地说:“我妈的病又加重了。” 杨力吃惊地问:“你妈病了?什么病?。” 翎子说:“医生说是呼吸道病,我也不懂,就是天天咳嗽,老停不下来。” 杨力“哦”一声,似乎想起了什么,却又没说。 翎子记起那天的事,说:“杨力,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,你们到底学到哪一课了?” 杨力立刻耷拉下眼皮:“我……” “怎么?这个也要保密吗?”翎子有些不高兴了。 杨力急忙说:“不。其实……我现在不上学了,我的课本是自己买的。” 什么!不上学了?翎子仔细打量着这个认识不到十天的新朋友:他高高的个儿,穿着及其普通的蓝布衣服,袖口上已经磨出毛边了;脸黑黑的,手也粗糙得不像一个天天坐在教室里的人。 她小心地问杨力:“你……为什么不上学呢?” 杨力的眼睛更低了。他使劲咬着发白的嘴唇,把一双大手搓来搓去,好像手上粘了蜂胶似的。他眼里含着泪花,但他强忍着,坚决不让它流出来。 “对不起,杨力。”翎子知道自己问了不该问的话。 杨力抬起头来,勉强笑了笑,说:“没什么,我得帮我爸取蜜去了。” (四) 这天早晨,翎子是被一群蜜蜂唤醒的。 昨晚翎子也没睡好,天快亮的时候,她居然做起梦来,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蜜蜂,在漫天的花蕊上采集花蜜。兴许是蜜采得太多了,飞着飞着,翎子觉得自己没劲了,眼看就要掉到地上时,不知从哪里飞来一群蜜蜂,把她托举起来,一同飞向无边的花丛…… “扑扑扑……”好像谁在拍打窗子。 翎子醒了。她推开窗户,窗外,一群蜜蜂在嘤嘤嗡嗡的,飞来飞去。哪来的蜜蜂呢?难道我的梦是真的吗?翎子简直要陶醉了,她觉得自己简直成了一位公主。这时,翎子看见窗前的木凳上有一个塑料瓶,里面装了一种淡黄色的东西。那是什么?翎子匆匆穿好衣服,迅速来到禾场坪。 翎子站住了。她像一杆瓜桩一样,在禾场坪里站住了。 她看见墨绿的芭蕉树后有一个人影。 是杨力! “听说蜂蜜可以治咳嗽。”杨力从芭蕉树后探出头来,指指木凳上的塑料瓶说。 翎子什么都明白了,她不知道说什么好,她很感激杨力的一片好心,可是…… 见翎子不说话,杨力以为她不相信,就说:“是真的,我爸说的。” 翎子为难地说:“可是……我没有钱。” 杨力说:“不要钱。” 翎子说:“那怎么行?等我爸寄钱回来,我就给你。” 杨力说:“是送给你妈吃的,不要钱。” 杨力走后,翎子连忙冲了一碗蜂蜜给妈喝。“这蜂蜜真甜,是河边养蜂人的吧?”翎子点点头,看着妈妈享受的样子,她心里比自己喝了蜜还甜。 从这天开始,每天早晨翎子醒来,窗外都有一群蜜蜂在迎接她,就像太阳那么准时。翎子推开窗户,就看见那些可爱的小精灵嘤嘤嗡嗡的,在空中不停地飞来飞去。有些调皮的,甚至飞进翎子的房间,落在蚊帐上,落在枕头上,仿佛它们也成了这里的主人。 可是,杨力却好久不见了,自从送来了那瓶蜂蜜,他就好像消失了似的。 每天早晨,翎子被一群蜜蜂叫醒之后,都要去河边做各样的事情。每次去河边,翎子都希望看到杨力,但每次她都失望了,除了杨力爸在忙上忙下外,什么人影也没有。 (五) 翎子开始变得慵懒了,每天早上,非要妈妈一催再催,她才肯起床做事。 这天,太阳已经爬上东山头了,翎子才端起木盆,有气无力地去河边洗衣。走到芭蕉树旁,她站住了。那次,杨力就是躲在这棵芭蕉树后面的,她还记得当时发现杨力的欣喜,可是现在,不知他到哪里去了,他难道回家念书去了吗? “翎子。” 忽然飘来一个细细的声音。 “翎子,是我……” “杨力!” 杨力从芭蕉树后面钻出来,头上顶着一片绿叶。 “你这几天上哪去了?”翎子急切地问。没等杨力回答,她就发现杨力脸上有隐隐的伤痕,手上也有一块淤青。“你这是怎么了?” 杨力淡淡地说:“没事。” 翎子说:“我是说怎么了,我想知道原因,快告诉我。” 杨力低着头,不言语。 “是被人打的吧,是谁?那个人是谁?”翎子越问越急。 杨力还是低头不语。 “是不是被你爸打了?是不是因为……”翎子想,这里很少有外人来,谁会打他呢?只有他爸了,一定是送蜂蜜的事让他爸知道了。 杨力抬起眼睛,戚戚地说:“我……不怪他。” 那天,他爸发现少了一瓶蜂蜜时,杨力就主动承认了。他爸二话没说,上来就是一顿拳脚。杨力没有躲,他知道爸爸不是要打他,是他内心有恨无处发泄。 翎子气呼呼地说:“不就是一瓶蜂蜜吗,我说过了,等我爸寄来了钱就给你。” “不!”杨力喊道,“不是钱的事,真的不是钱的事。” “那是为什么?” 为什么?我爸恨我妈,恨女人。可这些,我能跟你说吗? 去年暑假,杨力随他爸到河北放蜂。9月,他回家上学时,妈妈却不见了。她受不了大山的贫穷,跟一个木材老板跑了。他爸万万没有想到,为了这个家,他一年四季候鸟一样在外漂泊,天南海北地赚钱,可是……从此,他就固执地认为,世界上的女人没一个好东西! 其实,杨力爸是个既善良又豪爽的人,走到哪好事做到哪,在养蜂人里面,口碑最好。每年春节,凡是他放过蜂的地方,都有人打电话来向他祝贺新年,只是杨力妈的离去,让他的脾性发生了改变。那天,他发完脾气后,杨力说: “你不也经常送东西给别人吗?有时还送一箱一箱的蜂呢。” 杨力爸说:“那是人家有困难!别人有难伸手相助,是我们养蜂人的传统。” 杨力嘀咕道:“翎子家也有困难,她妈咳嗽半年多了,没钱买药。” “真的吗?”杨力爸的语气一下软了许多。 杨力说:“你忘了吗?我们养蜂人也不兴说假话的。” 杨力爸就沉默了。他的眼睛里,立刻发出一种柔和的、慈祥的光,过了好一会他才轻声道:“你,为什么不早说呢?” (六) 天越来越热了,山里的野花渐渐凋零,刺桐木也慢慢结出了小果。 这天,翎子在河边打猪草,杨力走过来说:“去我们养蜂场玩吧,我教你养蜂。” 翎子迟迟疑疑地,不置可否。杨力说:“放心吧,我爸今天去镇上了。” 养蜂场依然有一股浓浓的香甜味,蜜蜂依然在飞来飞去,只是翎子不再害怕了,她似乎与蜜蜂有了一种特殊的亲近。 杨力取出一个碟子说,“这是喂蜜蜂的。” 翎子有些奇怪,问:“蜜蜂不是给人类酿蜜的吗,怎么还要喂呢?” 杨力说:“晚上蜜蜂不采花,不喂就会饿死,尤其是花期过后,没有找到新的蜜源植物前,更要喂得勤快。” 翎子点点头。 杨力说:“你不要小看这个碟子,它可以指定蜜蜂采蜜的地点。” “真的吗?”翎子觉得杨力是在吹牛。杨力就告诉她,如果想要蜜蜂去某个地方采蜜,就把那里的蜜源植物的花瓣采一些来,跟稀释了的蜜汁和在一起,放在碟子里。每天早晨蜜蜂出巢前,把这个碟子放进蜂箱里喂它们,几天后,它们自己就会去那个地方采蜜了。 “啊,这么神奇!” 杨力说:“那当然!现在你家是不是天天有蜜蜂?那就是我引过去的。” “哦!我说那些蜜蜂怎么突然到我家来了,好像认得我家似的,原来你是向导啊。” 杨力又取出一块隔板,用竹刀拨下一坨蜂蜜递给翎子,说:“尝尝吧。” 翎子接过绵软的蜂蜜,并没有立刻放进嘴里,而是细细地端详。她想了起妈妈,妈妈吃了杨力送的蜂蜜后,咳嗽似乎好一些了。要是妈妈能坚持吃下去,兴许病就会好起来的,可是,哪来那么多蜂蜜吃呢? 杨力好像看穿了她的心思,指指蜂箱说:“吃吧,还有很多哩。” 翎子把蜂蜜放进嘴里,舍不得咽,她就那么含着,慢慢细细地享受。蜂蜜真甜,还有一股刺桐木花的香味。 (七) 又是一个如烟的早晨。 翎子在一群蜜蜂的陪伴下,蹦蹦跳跳地去河边洗衣。 走到半坡上,她突然“啊”地一声惊叫起来。此时妈妈还睡在床上,她被翎子的叫声吓坏了,赶紧爬起来问:“发生什么事了?” “他们——走了……”翎子无比伤心地说。 翎子和妈妈一起来到河滩。昨天还热热闹闹的河滩,此刻沉寂得没有一点声息,房子不见了,蜂箱不见了,杨力和他爸也不见了。他们就像两个神秘的侠客,来的时候从天而降,走的时候无声无息。翎子的心一下子空了,好像丢了一件最最重要的宝贝。 这时,几只蜜蜂忽然飞到翎子面前,围着她转圈儿,转了几圈后,它们离开翎子,径直朝一棵刺桐木飞去。翎子突然觉得一束灵光闪过,她立即追过去,一看,霎时惊愕了! 刺桐木旁,静静地卧着一只蜂箱! 那只被漆成草绿色的蜂箱上,无数的蜜蜂在爬上爬下,钻进钻出。 妈妈走过来说:“他们忘记搬走了吧。” 妈妈的话,翎子没有听见,她脑子里尽是杨力的影子。“吃吧,还有很多哩。”想起那天杨力的话,翎子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。杨力教她养蜂时,她只是觉得好玩,她一点也没想到,杨力是在实施一个关于她和妈妈的计划。 “杨力,你们去哪里了呢?你们……还会来吗?”翎子在心里一遍遍地问。 此刻,在一条通往山外的公路上,跑着一辆装满蜂箱的汽车。驾驶室里除了司机外,还有一对父子—— 父亲说:“我在刺桐木下留了一箱蜂。” 儿子说:“我知道。” 父亲说:“不知她们会不会养。” 儿子说:“会的。” 父亲问:“你教过他们了?” 儿子答:“是的。” 父亲问:“你怎么知道我会留蜂给她们?” 儿子答:“因为我是您的儿子。”
我写《回家》(创作谈) 陶永灿 去年深秋的一天,文联陶主席、东东、国佬等几个朋友约我去小水放间网,因为还有点事没处理好,我是后面骑摩托去的。回家时已近半夜,我的摩托没有灯,只好暂时放在我们吃饭的小店。 第二天,花队用摩托带我去小水,骑我昨天放在那里的摩托。到了小水,我们又到昨晚网鱼的地方转了转。已是傍晚,穿过竹林,看见红红的、圆圆的太阳缓缓西下,好像一幅水彩画,美丽极了,我们饥渴似的拍了不少照片。斜斜的阳光透过竹林,洒在小河边,把芦苇照得又红又亮,感觉非常温暖。这一景致,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,简直无法从脑海里抹去。我一定要写点东西出来,我想。 以前也是这样,看见什么无法忘怀的东西,就总在脑子里想啊想,这应该能写个东西出来的。当然,一开始不一定有什么眉目,比如是写小说、散文还是诗歌?用什么样的文学语言?这个文学语言怎么获得?是写给谁看的?等等。其实这就是一个思考、提炼、构思的过程,这个过程在写作中是非常重要的,也是非常艰苦的。我过去写文章,好多好的构思、好的句子都是睡觉时想出来的,一想出来,就马上起床记下来,有时一个晚上起来三四次。这是有道理的,睡觉的时候特别安静,便于思考;另外人睡觉的时候思维特别活跃,所以有人曾建议联合国开会躺着开。古人也说过读书“三上”的话,马上、厕上、枕上。 几天以后,我写出了《回家》。 写以前,我就定好了:一、写散文;二、给学生看,也就是儿童文学吧。 散文有很多种,我没有写所谓的“六要素”,方方面面前前后后都写到,那样的文章司空见惯了,没用的信息也太多了。我只是撷取三个画面,好像三副照片一样,中间跳跃性很大,用一、二、三标出来。用了那种空灵、优美的语言,有一点诗的味道,我把它归为意境散文。这样的文章短小精悍,语言漂亮,意境优美。 写儿童文学,得弯下自己的“腰”,体会儿童心理,俯身跟儿童说话,用少年儿童的语言来写。儿童语言有个显著特点,就是“童话”化。比如太阳就是太阳公公了,月亮就是月亮奶奶了,这本身就是拟人,就是一个童话形象。成人是不会喊太阳公公的,除非幼儿园的阿姨。 这样短小的文章,有几句漂亮话,有一个好的意境也可以了,这叫做唯美。这也是前两节的内容。但是,我在写作的时候,忽然想起我们小时候,傍晚山村里的景象:屋背上升起缕缕炊烟,村路上牛啊、鸭子啊都一边叫一边慢慢回家,做工的大人扛着柴或挑着畚箕或扛着犁耙朝家里走……于是,我自然而然加上了第三节: 望见瓦背上升起的缕缕炊烟,孩子们加快了回家的脚步。 奶奶,请您让炊烟飘得更高一些吧,让打工的爸爸妈妈,在城里也能看见。 让我自己也想不到的是,我那么自然地想到了留守儿童,想到了打工的爸爸妈妈,想到了当前中国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。现在想起来,这也并不奇怪,因为我一直在关注孩子,关注留守儿童,关注中国的教育等问题。而恰恰是第三节几句话,让这篇短短的文字有了更深的思想内涵和思想意义,也有了同情,有了爱。前面一、二节是写物,后面第三节是写人;前面是写自然,后面是写社会;前面是风光照,后面是生活照;前面只有美,后面还有爱;前面只有“意思”,后面就有了意义。最能打动人的地方,恰恰也是最后几句话。有几个在外打工的人读了《回家》,说眼泪都出来了。 写到这里,我自己也感到吃惊,因为是一中夏老师要我谈所谓经验时,才这么去分析、才惊喜地发现一二节和第三节之间的区别和意义的,我原来写的时候,根本没有这么理性,只顾一口气写下来。 最后说一点,我之所以选择用这种散文诗似的意境散文,是因为那段时间我喜欢上了那样的文章,喜欢上了那种空灵、优美的诗一般的语言。那段时间,我还写了《山村小景》、《秋天的味道》等。
附一: 回 家 (一) 外出旅行了一天,太阳公公要回家了。 老远闻到月亮奶奶的高粱酒,他就醉红了脸。 (二) 太阳公公下山的时候,在河边点燃了一支支蜡烛。 于是,那些火红的芦苇花,把回家的路照得通亮。 (三) 望见瓦背上升起的缕缕炊烟,孩子们加快了回家的脚步。 奶奶,请您让炊烟飘得更高一些吧,让打工的爸爸妈妈,在城里也能看见。
附二: 山村小景 打鸣 天刚麻麻亮,公鸡就吹响了起床号。那嘹亮的号声如同一只淘气的小皮球,在山里人家的屋顶上,蹦来蹦去。 于是,爷爷的咳嗽声醒了,灶膛里的火种醒了,草尖上晶莹的露珠也醒了。 “哐啷”一声,守夜的门闩开始下班休息,而早起的山里娃则坐在门槛上,捧出书本,又翻开了新的一页…… 洗澡 早上一起床,小鸭就成群结队地,去村外的小河里洗澡。 它们叽叽嘎嘎地,一会儿划动双桨,一会儿扎进水里;一会儿把水浇到自己脖子上,一会儿又互相打起水仗。那欢快的样子,让岸边的小鸡羡慕不已。 奶奶对我说过,早上洗澡的孩子长得快。小鸭小鸭,你们是不是也听到了奶奶说的话? 守护 大人做工去了,小孩上学去了,此时的狗,成了村里唯一的主人。 它真是一个称职的主人哩。 你看,它不是在村路上不停地巡逻,就是趴在村口站岗放哨。看见谁家的鸡偷吃粮食,它会毫不犹豫地把它赶走,看见村外有人来了,它就上前大声招呼。只是它的态度实在过于热情,常常让来访的客人心生畏惧,望而却步。 反刍 鸡睡觉了,狗睡觉了,喜欢在村里跑来跑去的风也睡觉了,只有勤奋的牛,还在复习功课。你看,宿舍已经熄灯好久了,可它还静静地坐在那里,把老师的每一句话,细细地、细细地咀嚼。 哦,我知道了,我知道了,它要把今天的知识全部消化,明天好学习新的内容。
作者简介 陶永灿,男,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生,瑶族,湖南绥宁人。创作以儿童小说为主,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黑喜鹊 白喜鹊》、小说集《有鸟的秋天》等。曾获第四届全国优秀少儿读物奖、1998年湖南省“五个一工程”奖,短篇小说《远方的云朵》获2001年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;多篇作品被转载,其中《泥鳅》入选《小学阅读指南》、《2006年中国儿童文学精选》及冰心奖获奖作家精品书系《新小说·青春阻击》。1994年加入湖南省作家协会。 |
||
联系电话:0739-7611972 湘ICP备14001922号-1 地址:湖南省绥宁县长铺镇工业街10号 湘教QS7_201311_001667